[A6A6I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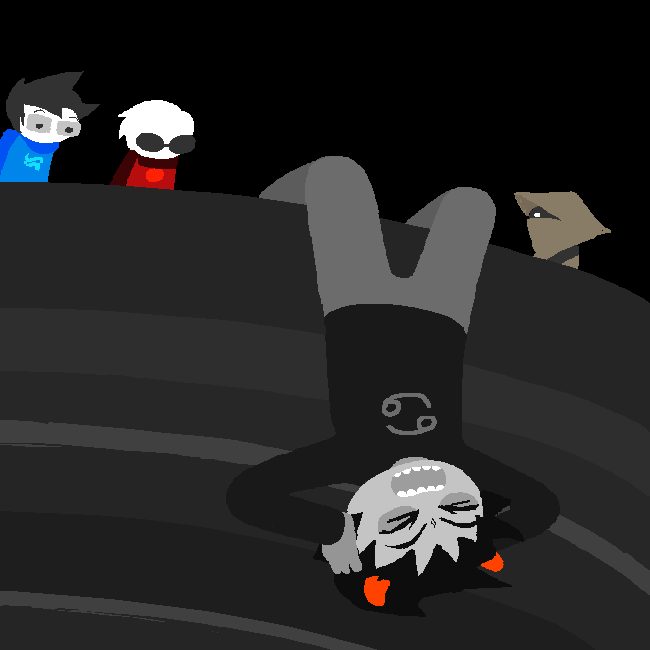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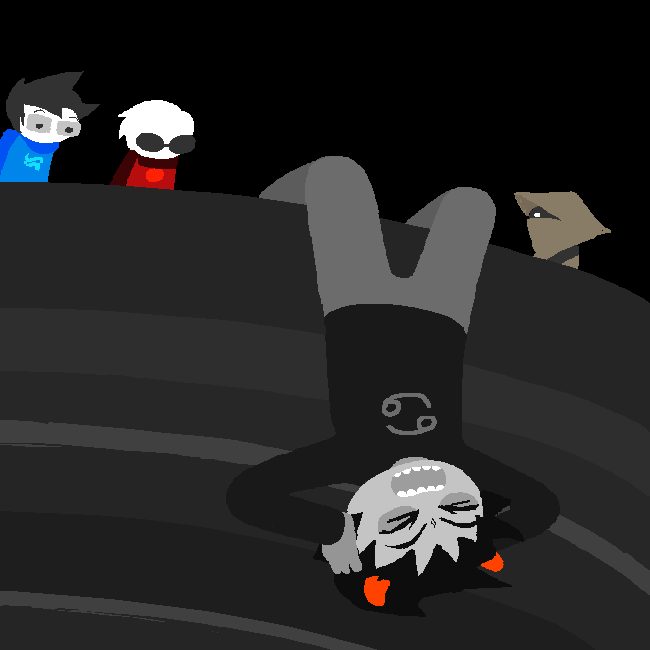
KARKAT:不,不,不,不,不,不,不。
KARKAT:我要撤退到我的安全屋,但是你们的狗屁废话。你们的愚蠢的操他妈的胡说八道就像吵闹的谷仓畜生一样蹂躏分隔我他妈的理智和最基本的个人界限的栅栏。
KARKAT:上帝诅咒的下流的幼稚傻瓜的呓语,它为何如此这般地萦绕着我悲惨的耳朵。这些屁话漫过这块魔法金属青蛙圆盘的侧缘,就像神秘森林中的一汪由渴求八卦而且挨了脑叶切除手术的霍比特人所守护的潺潺泉水。这如大河一般滔滔的话语从两个没脑子的爱哭鬼的失禁缝隙里渗漏出来,开始泛滥,哦,它怎么就泛滥了,它浸透了我真实存在的灰色裤子,一个朴实的人的腿部服装。一个朴实而且地位卑微的人。然后大河继续下流,浸湿我那平凡的衬衫,一个普普通通的艾特尼亚“老兄”的耐穿的服装,冻僵了衬衫之下的脆弱躯干,一条可悲的肉体,包裹在沉重的啜泣之中,那是被你们的狗屎发言诱发的啜泣,而狗屎发言永不停止地流淌,流淌。它蓄水。然后满溢。威胁着要把淹死。不是威胁,是保证。是誓言!但我却没有被淹死。为什么我不能被淹死?请淹死我。让我死这样我就不用再继续旁听这场狗屎烂蛋了!
JOHN:dave,我非常确定现在我们的对话让karkat感觉很不舒服。